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7月24日晚上7点,浙江省文化馆西湖文化广场馆区,杭州语言文化课教室里座无虚席。台上一位年轻老师正在带领学员们用杭州话读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
学员的年龄参差不齐,有七十岁的萧山阿姨来学杭州话的,有二十出头的杭州女孩不会说杭州话,这会儿想来学的,还有一位在社区医院工作的河南阿姨,为了和杭州女婿搞好关系,特地来学的。
“即便桌上摆的是一碗红烧肉,杭州人也会说成‘菜蔬’。”
“‘服帖’在杭州话里有两种意思,一种是衣服穿在身上很妥帖,一种是我服了你了。”
这个课堂妙趣横生,有几个“混进来”听课的杭州人也被吸引住,原来杭州方言里有噶许多文章!
台上这位老师叫高任飞,是1998年生的杭州小伙子,目前正在攻读语言类硕士。他是研究杭州方言小有名气的年轻学者。他不光研究杭州话,还用杭州话搞创作,写的散文、小说都毛有看头嘞!
下面是高任飞和我们分享的阅读故事。
我就喜欢说杭州话,更喜欢推广杭州话
口述 高任飞 整理 戴维
1
我小辰光住在孩儿巷。早上起来吃碗馄饨,放学出校门买一杯贡丸汤。走在巷子里,碰到认识的大伯大妈,嘴巴甜一点,还会讨到一颗糖、一块巧克力。
我从小喜欢看书。语文书拿到,第一件事先把全部课文看一遍。
初中我买的第一本书是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。初二我读了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万句》,模仿他写了一篇《咸豆浆和甜豆浆》。
我发现,北方作家用方言不太顾忌,像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莫言,对方言都是信手拈来。南方作家用方言,就比较斟酌,因为和官话相差太大。
有没有可能用杭州话写一本书呢?我当时有了这个想法。
2
2015年,我接触到百度贴吧上的“吴语吧”,很多吴语区的网友在上面发帖。
杭州话、苏州话、上海话、宁波话、常州话、绍兴话、无锡话等一系列子方言,同属于吴语的太湖片。生活在“长三角”包邮区的人,每个人讲着家乡的吴语,有时居然能互通,比如“假痴假呆”“轧闹猛”。
我和一些热爱方言的朋友做了一个吴语辞典网站,叫“吴语学堂”,把各地的吴语方言都囊括了。从那时起,我开始系统性研究杭州方言。
我曾经到梅家坞一带特意寻访杭州话的古音,找到两位九十多岁的老爷爷。他们说的话比城里的杭州话发音更古老,比如“三”“山”都带鼻音,“江”“糖”的发音位置更高。
从老爷爷那里,我还学到了杭州话的“仲人儿”,是以前坟墓前的石人像,也叫“石翁仲”,因为一动不动,后来有了“呆若木鸡”的意思。
3
很多人有种印象,杭州话讲小热昏是可以的,比较下里巴人,但要是用来搞文学创作,好像差点意思。2019年,我开了公众号“杭州话语”,里面有我用杭州话念的古诗,还有我用杭州话写的小说。
《点香烛》讲的是杭州一家陈姓糕点店和耶稣堂弄里洋教士的故事,普通话“花掉在床上”,我用杭州话写成“花跌落在眠床高头”。
《杭味廿篇》是二十个短篇,写的都是杭州的点心,比如小笼包,猫耳朵,烧饼油条,拌面,油墩墩儿。每一种我都编了一个故事。《烧饼油条》这篇的开头是这样的:
清早八早天也没亮,门口头只小狗儿还孵(bbu,意为孵蛋) 徕没爬起。楼底下早饭店夹了葱花味道的油水气,老早徕哈墙门里荡开,暗落落个从门缝档里躬(gang,意为钻进去)进来嘚。气息汆(ten,意为漂浮或油炸)满客堂间,渗到里间,倒灌进鼻头,沿着头颈骨头直冲脑髓,好比一只铜铃儿徕骷䯖头里拉警报。阿董乌珠“啪”个挖开,被头攉(huoh,意为甩)掉,看看肚皮仍番瘪塌塌,两块巴掌肉倒是涨佬佬,口流水盛不落,要汆出来。豪稍弹起,畀衣裳套上,驮来洗脸洗盥。胡须好来不及刮——早点心是捱板要吃的。
不少人喜欢用普通话的读音去写杭州话,下雨写成 “六鱼”,其实应该写成“落雨”;洗澡写成“大玉”,应该写成“汏浴”。
虽然错别字的发音一样,但杭州话实际上是有正字的。乱写一气,是要贻笑大方的。要是不会写杭州话,大家可以去“吴语学堂”网站搜一下杭州话辞典,可以找到正确写法。
4
今年2月,我在浙江省文化馆开了一个杭州话普及班。听说名额很难抢,一个班30个人,有400多人报名。
我教学生说杭州话,先把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告诉他们。秦汉时期,浙江人才开始讲汉语。但是一千年来,杭州方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北魏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里提到“吴人自呼阿侬”,明代顾佐的《西湖竹枝词》中也出现了“阿侬心似湖水清,愿郎心似湖月明”。可见,当时杭州人叫自己“阿侬”。如今,金华等地区的吴语还自称“阿侬”。
再比如清代学者翟灏编的《通俗编》中,提到元代札记《辍耕录》记载的一些俗语,如今大多不存,“杭人好为隐语,如粗蠢人曰‘杓子’,朴实人曰‘艮头’”。
“杓子”和“艮头”的说法,到清代就消失了。现在杭州话的框架到清代末期才正式形成。
20世纪50年代初,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一部电影《三毛学生意》,里面有个讲杭州话的算命瞎子,是范良益先生扮演的。范先生是1907年生人,他在电影中的杭州话口音就和现在有所区别。
5
杭州话是比较古老的汉语方言,至今保留了七个声调,也难怪北方朋友难学了。
唐宋古汉语的清音和浊音,在杭州话里也被保留下来了。比如丝绸的“丝”是清音,是不是的“是”就是浊音。
有的学生学得蛮好,进步蛮快。我和学生说,语言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,你们不要光看教材,要去听语言,到自然环境下听。
我推荐他们去看一本很老的杭州话电视剧,20世纪90年代拍的《老房子新房子》,讲当年中东河拆迁的。还可以看杭州电视台的新闻节目《我和你说》《阿六头说新闻》。
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逛马路。我住在河坊街一带,平时喜欢骑上电瓶车四处闲逛,周围是中山中路、鼓楼、大马弄、十五奎巷,可以说是“老杭州生活气息保护区”。
杭州话的特点是说起来爽快,有侠气。这种侠气是隐没在市井里的,靠着老墙门才能生根发芽。
要说热爱传统文化,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劲头很大。有些人觉得,研究方言的都应该是老专家、老杭州人。我是杭州人,直直不算老,但我就喜欢说杭州话,更喜欢推广杭州话。
所谓乡愁,一半是食物,一半是语言。离开杭州话,我会想念的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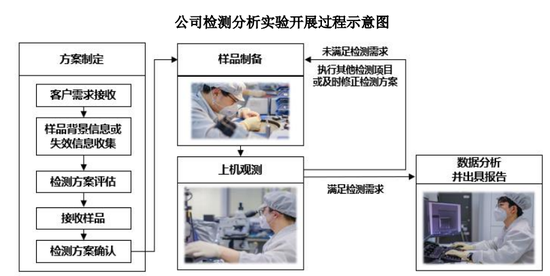

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
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
京ICP备11000001号